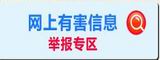三十年前中師畢業,最要好的同學突然申請到甘孜州新龍縣支教。之前從未聽他提起,也不好向其打聽。同學雖有一顆詩心,裝著遠方,不至于如此耍酷只身向西行。即便我們當年好到可以同穿一條褲子,至到現在我都未問及,緣何要去那陌生之地。
那年夏天,我們靠著書信往來,想象西出陽關之類的送別,懷著美好,亦有凄涼。再次收到同學來信時,他已長途班車,三天勞頓,到達了支教之地新龍縣城。報到通知如同他支教決定一樣突然,省城專職機關要組織餞行會,故而匆匆前往,來不及將預想的道別付諸行動。
一場可能由縣城到省城,再經甘孜州府康定而新龍的送行,就這樣被信息與交通的不便,無情粉碎。所謂的桃花潭水灞橋折柳,終究是一場青春遺夢。
同學乃典型文藝青年。熱愛文學,詩歌小說筆耕不輟。鐘情音樂,寫歌作曲彈唱自如。令我佩服的是一首流行歌曲,聽上幾遍,不單能唱,還將曲子寫下。有一年冬天,同學受邀去北方參加筆會,路費成了問題。我逃課坐車趕至父母趕集的場上,軟磨硬泡從他們并不寬裕的手中拿走200元現金,讓同學筆會如期成行。赴會途中,同學書信告知心情見聞。可惜我沒有保存那些書信。多年之后,我不止一次想象,同學趴在列車座椅前寫信的場景。去遠方的激動、喜悅與憧憬,隨時傳遞。
同學的詩歌我不常讀,倒有一部小說,我是第一讀者。手寫文字鋪滿了厚厚的作業本,不多的人物中仿佛有他的影子,似乎有我,還有一位女生。情節已不清楚,大概率屬于我們的青春之歌。不知道那部手稿同學是否保留,還想細細品味。
中師三年于我,別無他求與人無爭地傻過著。當知道自己三年后的歸屬為某所鄉村小學的三尺講臺時,即便心有不甘,亦無波瀾。自我要求不高的是,聽老師的話,聽學校的話,老老實實過完三年。因此,教科書成了我最大的閱讀偏好,卻陰差陽錯幫了一個大忙,每個學期考試成績還不錯。在那個主要以分數和平日表現看人優秀與否的年月,我憑此居然得以保送上大學的機會,多少有些令人意外。
同學去了九龍,我去了大學,書信依然是我們的日常守候,一封接著一封。他用文藝的筆調描繪著陌生之地的新奇、孤寂與熱血,我用慣常的話語聊及大學生活的自在、落寞與惆悵。三年中師,學習生活無不虛度,進入大學有些適應不良而心生焦慮。他盼我去新龍,我盼他來大學校園。我們約定兩地見面,將曾經來不及的送別化作重逢。
過兩年,同學離開新龍,離開了那片銘心刻骨的土地,也離開了那里某位姑娘的深情。同學來信說幾乎是不辭而別,好不容易靠著求學換來的身份編制就此拋棄。即便雅礱江水仍然沸騰內心,各種不適終歸難以久留,離開算是對當年突然決定的徹底了結。收獲體驗,珍藏信仰,一切重新出發。
同學去了南方,進入工廠開啟打工人生活。從靜謐苦寒的高原到枯燥乏味的工廠,百般滋味、千般苦楚,究竟是怎樣的一場涅槃,同學避而不談。回避不了追問時,也是云淡風輕。倒是一個勁地鼓勵我,珍惜大學生活,將來謀個像樣的前途。
中師生保送上大學,如無它途,畢業注定回到保送之地。如是那樣,實非我愿。心既不甘,便起波瀾。考研是不錯的擺脫之道,我把大把時間花在影視文學專業研究生備考中,學習生活貌似充實踏實。中師三年停學外語的硬傷,總分雖及,但外語單科未過,最終落榜。求得保送學校同意,償還委培費用,方獲不受限的找工作資格,總算留在了大學所在的城市。
同學經過我的工作之地,我們期待見面時的酣暢痛飲秉燭長談,卻成了彼此沉默的無言以對與嘆息。想說的話不知從何說起,只能用逛街化解多年等來的尷尬。時間改變著一切,誰也抵擋不住。曾經無話不說的我們竟然無話可說,錐心的疼痛刺激麻痹的神經,彼此都想要盡快逃離那漫長的兩天。還有什么可說呢,生活已將我們錘打得不再是當年理想豐滿青春氣盛的模樣。
那之后,我們沒有見面。快節奏的生活,書信不再是我們的守候,偶爾的信息往來多是問候。同學還保存著那顆詩心,詩歌在他的朋友圈一度常見。少了抒情,多了經歷之后的沉淀。朋友圈中的我呢,多是一些花花草草,一如當年校園時的嘻嘻哈哈。
自駕去了一趟川西,六個小時到康定。車過九龍,美滋滋拍照發與同學,并附言:三十年后走了一趟三十年前兄弟走過的路。同學回復:那時一眼望去,滿目荒涼,確實沒有勇氣呆下去。現在變化應該是很大了吧!
想是同學工作故地,引發過往記憶,遂在手機上斷續記錄,不時將片斷發給同學。回家翻看舊日書信,才發現自己鬧了烏龍,錯把九龍當成新龍。記憶不可靠,喜悅瞬變沮喪。同學言:新龍更偏僻一些,之所以沒有糾正,實在是覺得差別不大,僅僅是距離上的不同,自然風光人文風情都差不多。
同學的厚道,成就了我美麗的誤會,就把九龍當新龍吧!肉眼可見的基礎設施,通訊和民居,變化明顯。不變的,是終年不化的雪山,是奔流不息的雅礱江水和從未停止的思念。
一念三十年。
(作者系重慶兩江產城建設有限公司監事會主席)

 四川法制網
四川法制網
 法治文化研究會
法治文化研究會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