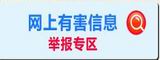人生走過幾十年,已想不起喝過哪些品類的酒,但最讓我懷念的,是20世紀80年代國營內江縣石子酒廠釀造的紅苕酒。
紅苕酒,又叫苕干酒,將紅苕搗碎放入大米和酒曲發酵,經15-30天,蒸餾而得。其色清亮透明,酒香獨特持久。
記憶中,我第一次喝紅苕酒是十來歲。爺爺和父親是愛酒之人,但都喝得不多。每周,爺爺都會給我幾毛錢和一個空酒瓶,叫我放學后去代銷店打酒。家里窮,打不起優質的高粱酒,只能打便宜的紅苕酒,我身上所帶的錢也只夠買半斤左右。
代銷店就在我們學校旁邊,賣酒的大姐姐叫熊永仙,人長得漂亮,熱情善良。店內的酒都是從石子酒廠拉來的,有紅苕、包谷、高粱、甘蔗、白芷等釀制的幾種散酒,各盛一壇,壇口用包有高粱米的大紅布袋捂著。每次打酒,一揭開蓋,那濃郁的酒香就彌漫開來,充盈店內,讓人口水暗流。有時放學晚了,代銷店已關門,我就站在店外的田坎上,扯起嗓子長聲吆吆地喊:“有人打酒,有人打酒啰——”不一會兒,熊姐姐就來到店里。即使在吃飯,她也會放下碗筷,快速趕來,她怕我們等久了。
爺爺和父親白天干活勞累,每天晚上都要喝兩口。打回酒來,到了晚上吃飯的時候,爺爺找來一個小粗碗,倒上一點點,約莫八錢,只能蓋著碗底。盡管很少,但爺爺都會叫上父親,父子倆輪流小飲,通常邊暈(喝)酒邊擺龍門陣,涉及主題大都為農事、做人。爺爺和父親喝酒,每次都輕輕抿一口,入口后吧嗒吧嗒的,很享受的樣子,久了我也有些羨慕,有一次問:“喝起很安逸嗎?啥子口味?”爺爺說:“安逸得很,你抿一下就曉得了。”說著就把酒碗遞給我,因為是第一次喝酒,我小心翼翼,淺嘗一口,入口瞬間,辣味直鉆喉嚨,但余味回甜,滿口烤薯焦香。從此,我記下了它的味道。
成年后,我時不時也會小酌一杯。好多次,我們三代人圍坐在一起,喝國營石子酒廠釀造的紅苕酒。那時,下酒菜就是壇子里的酸蘿卜、泡海椒、酸娃娃菜,現在想來很寒酸,但那時我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20世紀80年代末,我外出讀書,到后來參加工作,很少回到老家,石子鎮的紅苕酒也就很少喝到了。90年代中期,國企大改革,很多企業接連倒閉,石子酒廠也不例外。
幾十年來,雖然身居在外,但石子酒廠的紅苕酒,依然在我的記憶深處飄香,揮之不去。每當和朋友聊起酒時,我都會幸福而自豪地談起它。
今年夏季,我突然有種沖動,想去石子酒廠看看。看看當年曾經釀造紅苕酒的車間以及釀酒設備,呼吸一下那曾經彌漫酒香的空氣,撫摸一下那段已經銹跡斑駁而溫情的歷史。但居住在石子鎮街上的好友告訴我,酒廠的廠房十年前就拆了,我有些黯然失落。
后來,我得知,國營內江縣石子酒廠,上世紀是原內江縣重要的工業企業。“石溪牌”酒在1985年曾獲得內江地區優質獎,遠銷省內外,為原內江縣的經濟貢獻過不凡業績。
我開始留意并打撈散落在民間的有關石子酒廠的史料碎片。前不久,我在內江甘泉寺古玩市場,“打撈”到一枚20世紀80年代石子酒廠的“石溪”酒標,非常精美,我捧在手里,倍感親切。后來,我又從藏友手中購得石子酒廠別的酒標,算是存留一份珍貴的史料記憶。
而今,石子酒廠和它釀造的高粱酒、紅苕酒、苞谷酒、蔗渣酒、白芷酒,雖然早已化作云煙,飄散在歷史的深處,但紅苕酒的醇甜馨香,依然流淌在不少人的記憶里。

 四川法制網
四川法制網
 法治文化研究會
法治文化研究會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