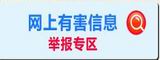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黎二愣
一
16757號(hào),落下閎星自蜀地閬中升起,在浩瀚星空撲閃撲閃,引發(fā)我的詩(shī)興,去對(duì)接落下閎星光的遙遠(yuǎn)與亙古。
落下閎星,不僅僅是聯(lián)合國(guó)天文學(xué)會(huì)授予和命名,西漢,華夏人已把他偶像成閃耀在中國(guó)天空的星。那時(shí)代追星的狂熱,比現(xiàn)代人當(dāng)票友、戲樓追劇更猛烈,他們把一生的敬仰和祈禱都跪給天上最亮、最親切的星星。
閬中“星座苑”是落下閎故居,亦是落下閎觀測(cè)天象的望遠(yuǎn)鏡,天與地,兩極兩儀,都被拘捕在“望遠(yuǎn)鏡”里。山川風(fēng)物,日月星辰,命運(yùn)都交給落下閎,在望遠(yuǎn)鏡里放大或者縮小。這里,是西漢天空的中心。
落下閎的八十一算法,每組數(shù)據(jù)的組織,都是管理星星的軌道。每一個(gè)星宿,都聽(tīng)從落下閎的指揮。于是唐代星象大師袁天罡、李淳風(fēng)來(lái)這里認(rèn)祖歸宗,把肉身和魂魄都寄托給落下閎,繁衍風(fēng)水學(xué)家和弟子。
閬中,又是中國(guó)風(fēng)水文化基地。那些天與地,地與人,人與天與地的輩分,那些穴與氣的真言,從閬中走,走向西北,走向中原,成為中國(guó)民間習(xí)俗。小小閬中,是中國(guó)民俗漣漪的核心,核心發(fā)多少力,漣漪就開(kāi)出多大的水花,風(fēng)水就在漣漪中生根發(fā)芽。
二
寓居巴蜀的落下閎,用《太初歷》為比例尺,把二十四個(gè)節(jié)氣劃定在天地間每一個(gè)位置。于是,從立春到大寒,每一個(gè)節(jié)氣就有了自己的姓氏,從此,人間四季分明。
山川與雨雪、陰晴與圓缺,莊稼與野草,人類(lèi)與動(dòng)物,各自春生夏長(zhǎng),秋收冬藏。生命有來(lái)來(lái)去去更迭,就有起有落,有由此及彼的永恒。《太初歷》滿(mǎn)篇是數(shù)字的排列,卻如一個(gè)哲人,在書(shū)頁(yè)里架設(shè)邏輯,不與唯物或唯心辯論,不與辯證與形而上斗嘴,也沒(méi)與無(wú)神論有神論爭(zhēng)辯。
無(wú)聲和沉默,有時(shí)是守護(hù)真理的衛(wèi)士。
漢武帝以自己年號(hào)“太初”,為落下閎的《太初歷》加封蓋印。落下閎抗著這枚印,在時(shí)空網(wǎng)中,紅了兩千年,一直昂首在天文歷史的扉頁(yè)。人們把他稱(chēng)為世界天文學(xué)的爺。
閬中,把這位爺不叫爺,而是叫做“春節(jié)老人”。
落下閎,把春天定位在正月。中國(guó),有了代代相續(xù)、年年同賀的春節(jié),閬中人,將人類(lèi)天文學(xué)的鼻祖叫做“春節(jié)老人”。
落下閎星運(yùn)行在天宇,我們?nèi)碎g,便知道天與地有多遠(yuǎn)的距離。
三
你不信地球是漂浮在水中或氣體中的,更不信“地有四游”之說(shuō)。你以青銅造出渾天儀,一半在地下,一半斜向天空,似地球上生出的一把木瓢,將一個(gè)個(gè)星星舀入懷中。
28個(gè)星宿很大,也很遙遠(yuǎn)。渾天儀以時(shí)間的齒輪,將天宇咬出28個(gè)坑,星宿被凝固在里面,渾天儀的窺管如射電望遠(yuǎn)鏡的定向天線(xiàn),成為28個(gè)星宿的根,任浩瀚的星際如流沙沖刷,這星宿穩(wěn)穩(wěn)地扎根中原大地,成為人類(lèi)與天宇通話(huà)的媒人。
渾天儀,是落下閎觀察天宇的眼睛。
渾天儀亦是大地與天宇連接的樓梯。
天上的鳥(niǎo)兒沒(méi)飛上去,地上的神靈也沒(méi)飛上去,唯張衡、李淳風(fēng)、郭守仁,借落下閎的視力爬上去,而且在天庭里,發(fā)現(xiàn)了更多的秘密。
閬中的星座苑,注滿(mǎn)嘉陵江的濤聲和歷代帝王的封賜。門(mén)楣上的匾額和聯(lián)句,華麗且樸素,錦秀且端莊,都是宋詞的格律,嚴(yán)謹(jǐn)?shù)眯⌒囊硪怼N矣糜洃浲仄@段光景,放入歷史的筆記里。雖然不能與《史記》《漢書(shū)·律歷志》所記載的故事媲美,卻可以讓我的仲夏繁星閃爍,聽(tīng)天宇里此起彼伏的蛙聲。
夏日的黃昏,斜陽(yáng)將閬中古城的影子在大地拉得越來(lái)越長(zhǎng)。恍惚間,我一抬腿,就踏上通向宇宙的天梯,連同我的心事,也越長(zhǎng)越高。

 四川法制網(wǎng)
四川法制網(wǎng)
 法治文化研究會(huì)
法治文化研究會(huì)



 川公網(wǎng)安備 51010402001487號(hào)
川公網(wǎng)安備 51010402001487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