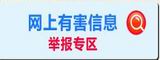今年到此為止。
12月的某天清早醒來,看著2023年已逼近封底,我突然想到了這句話。樓下的銀杏葉已在草地上鋪了厚厚的一層,街邊的小面館、早餐店正熱氣騰騰,送孩子上學的、出門上班的,在冬日的寒冷中開始了新的一天。
那幾天剛好遇到氣溫斷崖式下降。自入冬以來,天氣不錯,稱得上是暖冬,街道上、公園里的海棠花七零八落的盛開,人們在適宜的氣溫里很是享受,自然還不適應突如其來的寒冬的凜冽,都紛紛喊太冷了、受不了。而我卻一聲不吭,只顧一件一件地添衣。我自己明白,今年我的冬天,是從夏天開始的。
5月藍花楹盛開的時候,患病兩年多的妻子去世了。忙完妻子的后事,我新疆、湖南、河南、北京到處走,努力從寒冷里走出來。有一件事烙在腦海里特別深刻:在成都東站我看見一只受傷的麻雀后,注視了它好久,煙一支又一支地抽。看見不遠處有一只麻雀飛過來,我想當然地,以為是尋它的伴侶。
當然我也一直清晰地記得,某個秋夜一場碎夢中的四個片斷——
夢見孩子還小,在學校參加接力比賽。賽場上,我居然帶著鍋、生上火,一邊關注著孩子比賽,一邊炒菜。絲毫不顧忌,濃濃的油煙,讓人們厭惡責怪、避恐不及。
夢見在菜市場和人搶蘿卜,最終把新鮮嫩白的三個蘿卜搶到手。
夢見下了雨,路面濕滑,自己騎摩托車摔了個人仰馬翻。面對搭乘的朋友的嗔怪,我嫌他太胖了,他反問我一句:再胖有你老婆胖嗎?
夢見自己泅渡在一條河里。水面不寬,河水不急,就是靠不了岸,只能向著遠處一個山坡用力撲騰,——那里是妻子的墳。
很長一段時間,我時不時的,暗揣、解析這四個夢的片斷。人近五旬的我,人生中有兩次成長:少年喪父和中年喪妻。少年不識愁滋味,相比見多了無常、經歷了各種際遇、“耳畔頻聞故人死”的中年,對生命、死亡的理解自然沒那么透徹。周海媚離世那幾天,網上鋪天蓋地的懷念和唏噓。對于不追星的我來說,起初尚不理解,后來恍然大悟。她是伴隨我們70后成長歲月的明星,我們不但是在緬懷自己的青春,而且清醒地意識到了,我們已經走過了前半生,正在生死間流浪著。
所以在妻子離去的整個夏天里,我比年少喪父時要痛得多,心里的寒冷不可與人語。在龍門石窟,我注視著大周許乾為已故夫人造的那龕石像,眼眶一陣潮濕,一條伊河水,在心里起了萬千波瀾。
已然被扔在半路上了,雖然意難平,但我必須放下執念走出來。上還有老、下還有小,我肩上的擔子還重著呢。我做不到“生命吻我以痛,我卻報之以歌”的豁達,在無數個輾轉反側的夜里,我告訴自己“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阿Q式的自我安慰:命運給我寒冷,或許是要讓我尋找溫暖、自己取暖。
往年的年底,如同莊稼人細數收成一樣,我要對自己的工作、生活進行盤點。今年太黯淡,我沒有追上,那個曾經發光的自己。今年的風太大了,我不想回頭看,不想注視深淵、又讓深淵注視我,只想說:今年到此為止,愿所有不好的事、難過的經歷和壞情緒都翻篇兒。
這幾天天氣還不錯,太陽很好,工作也很忙。期待新的一年,無論我往哪個方向走,都是迎著光向前、向上。(李美坤)

 四川法制網
四川法制網
 法治文化研究會
法治文化研究會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