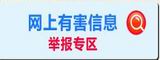天壇公園里有一個(gè)白色的藤蘿架,那是我的“客廳”——無論春夏秋冬,無論之前是否相識,我總能在這里碰到聊得來的人,即使是萍水相逢,卻也相見甚歡。
一天,快到中午的時(shí)候,我坐在藤蘿架的一側(cè)畫畫兒,突然發(fā)現(xiàn)一個(gè)身穿黑色連衣裙的女人,她正扭動腰身,拿著手機(jī)自拍。在她身后有茂盛的藤蘿,藤蘿后面還有幾棵高大的雪松,它們將陽光密實(shí)地遮擋。那一大片藤蘿葉綠得格外濃郁,如同深沉的湖水在微風(fēng)中抖動,泛起微微的漣漪;間或有陽光從綠葉的縫隙間擠進(jìn)來,灑在她的身上和地上,斑斑點(diǎn)點(diǎn),像跳躍的銀色小精靈。女人的身材苗條而玲瓏,她頭頂漁夫帽,脖子上戴著珍珠項(xiàng)鏈,顯得很有朝氣。
我正打算畫她和她身后的藤蘿,她卻徑直向我走來,和我打招呼,仿佛老朋友或老街坊那般熟絡(luò)。這就是北京人的秉性,大多不設(shè)防,“自來熟”,兩句話都能把彼此的距離拉近。
我趕忙站起來,指著她手里的手機(jī)說:“我看您自拍來著,我?guī)湍諒埾喟桑 ?/span>
她把手機(jī)遞給我,說:“好啊!自拍把人照得特別大,景兒卻照不全。”
我?guī)退牧藘蓮垺J謾C(jī)屏幕上的人,比剛才在遠(yuǎn)處看的人顯得歲數(shù)大很多——距離,時(shí)常能迷惑人的心和眼睛。
“您看看,我照得行不行?”我把手機(jī)還給她。
她看了看,說:“您照得挺好的,還帶‘美顏’了呢!”她沖我一笑,接著說:“昨天我在家里臭美了一天,我家老頭兒說我整天就知道臭美!您說,這么大歲數(shù)了,再不臭美,還等什么時(shí)候美?”
我應(yīng)聲說:“您說得對,年輕時(shí)沒法美,現(xiàn)在再不美美,待到何時(shí)!”我本想問問她多大歲數(shù),但貿(mào)然問女人的年齡不太禮貌,只好把話又咽了回去。
她一邊說,一邊在手機(jī)相冊里找昨天拍的照片給我看。照片上的她化著濃妝,面部讓脂粉修飾得過于白嫩。不過她的眉眼很周正,尤其是那雙大眼睛,想來她年輕時(shí)一定是個(gè)美人。
她笑著說:“您看是不是臉太白了,我回去還得再調(diào)調(diào)。”
我說:“是!調(diào)調(diào)您就更美了!”
她笑得更厲害了,說:“這不,今天我就是到天壇來臭美了。出門前,我家老頭兒說我昨天美了一天,怎么還沒美夠啊!”
我問她:“怎么您家老頭兒沒和您一起來?”
“他在家做飯呢!”
“哦!敢情您自己在天壇美夠了,回家吃現(xiàn)成的,您可真夠美的!”
她笑得花枝亂顫。
忽然,她對我說:“跟您說,外面推銷的保健品,千萬別買!人老了,最好的保健是食療,您說對不對?”
我趕忙點(diǎn)頭。
“快到中秋節(jié)了,每年這時(shí)候,我一準(zhǔn)兒去懷柔的四道河買栗子。那兒到處是賣栗子的,很便宜,去年是五塊錢一斤,我一下就買了二十斤。”
我問:“栗子可不好保存,您是怎么保存的?”
“栗子剝了皮放到冰箱里,每天吃五六顆,能吃一整個(gè)冬天。這東西有營養(yǎng),補(bǔ)腎氣!”
我又問:“您買這么多怎么帶回來啊?”
“孩子開車帶我們?nèi)パ健H绻⒆硬蝗ィ揖秃臀壹依项^兒到東直門坐長途汽車,一人背一包回來!”
我挺驚訝:“您和您家老頭兒真厲害,身子骨夠棒!我不行,比不上您,不過今年我也得去四道河買點(diǎn)兒栗子嘗嘗。”
我們兩個(gè)人都笑了。
她的日子過得這般悠然自得,實(shí)屬不易。我望著她,又忍不住猜測她的年齡,便轉(zhuǎn)個(gè)話頭兒問她:“咱倆誰歲數(shù)大?”
她快言快語:“我1952年出生,屬大龍的。”
“今年整七十歲了!”我順著這個(gè)年齡往前算,接著問:“您是69屆的?”
“是。”
“那您插過隊(duì)了?”在我的記憶中,69屆的學(xué)生幾乎都去農(nóng)村當(dāng)知青了。
“沒有!我的幾個(gè)堂姐去山西、陜西插隊(duì)了,可我媽不讓我去。咬牙熬了不到兩年,給我分配的工作。”
“您在哪兒上班?”
“烤鴨店!”
“好地方呀,烤鴨您一定沒少吃!”
她忍不住地笑。
我沖她豎起大拇指:“還是您母親厲害!”
“我媽沒文化,就認(rèn)準(zhǔn)了不讓我走。我的幾個(gè)堂姐后來都從農(nóng)村回來了,自從結(jié)婚生小孩,發(fā)愁的事兒一個(gè)接一個(gè)……幸虧我家有個(gè)小院兒,父母去世前把小院兒分給幾個(gè)孩子,現(xiàn)在都租出去了。房子倒是沒發(fā)過愁,愁的是孩子!”
沒想到一說房子,“拔出蘿卜帶出泥”,扯出新的話題。她是個(gè)心直口快的人,藏不住事,立馬說起他的兒子:“我兒子四十多歲了,有兩個(gè)孩子,一男一女;老大上高中,老二上小學(xué)。這兩個(gè)孩子都是兒子和兒媳婦自己帶大的,我沒受過一天的累。”
“多好啊!您這是享清福,坐等孫子孫女長大,有什么可愁的?”我對她說。
她說:“有了孩子之后,我兒子不讓我們帶,他說孩子必須跟在父母身邊。兒媳婦本來有個(gè)挺好的工作,我兒子非讓她把工作辭了,在家里一門心思帶孩子。”
“原來是兒媳婦當(dāng)了全職太太。您兒子是做什么工作的,能負(fù)擔(dān)得起這么大的開銷?”
“做金融的。”她只輕描淡寫地一說。我想,金融行業(yè)的收入肯定不錯(cuò),應(yīng)付日常開銷并不難,便對她說:“這不是挺好的嗎?”
我察覺到她輕輕嘆了口氣,不過轉(zhuǎn)瞬間就像小風(fēng)一樣吹過去了。
“我兒子說孩子必須跟在父母身邊,這話的意思您可能不知道,可我明白,這和他的童年經(jīng)歷有關(guān)。”
確實(shí),每個(gè)人都像一本厚厚的書,乍一看,封面都挺堂皇;一打開,各有各的跌宕。
“他從小跟著姑姑長大,上初中后才和我們一起生活,和我們一點(diǎn)兒都不親。我跟他解釋過好幾次,我和你爸爸工作忙,而且都不是朝九晚五的正常班,上幼兒園、上小學(xué)時(shí),我們沒法按時(shí)接送你,只好把你送到姑姑那兒……他聽完不說話。平時(shí),他這個(gè)人挺能說的!”
不說話就是一種心情、一種態(tài)度,做母親的,心里自然跟明鏡似的。
人這一輩子,必要的酸甜苦辣得全部嘗過,才算經(jīng)歷了完整的一生。生活不可能都是蜜一般的甜,也不可能都是黃連一般的苦;即便是再平緩的水流,也不可能都是“潮平兩岸闊,風(fēng)正一帆懸”,總會有些風(fēng)浪,哪怕打不翻這葉扁舟,也得吹皺一湖漣漪。這就是人生的“能量守恒定律”吧。
其實(shí)在我看來,這個(gè)女人的一生已經(jīng)算夠美滿的了。但母子連心,兒子童年那些經(jīng)歷所刻印下的性格的深痕以及母親心中那無法彌補(bǔ)的愧疚,就像小蟲子,時(shí)不時(shí)爬出來,咬噬著這對母子的心。對兒子心頭的這個(gè)“疙瘩”,她并沒有奢望讓這個(gè)疙瘩變成漂亮的蝴蝶結(jié),只想著不是死結(jié)就行,能松一松更好。可疙瘩就是疙瘩,伴隨歲月的延展,越來越難解開。不過能有什么好辦法呢?做母親的,只能自己慢慢消化,與內(nèi)心達(dá)成和解。在我看來,她的臭美,便是自我消化的一種手段,與內(nèi)心達(dá)成和解的一張藥方。人這輩子,最大的對手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是自己的心。誰的心都不是一塊柔滑的絲綢,哪怕沒有千瘡百孔,也多多少少留有一些褶皺。
她將這番心里話吐露之后,似乎痛快了許多。萍水相逢的人,最適合說這些對親人、對朋友很難說出口的話,雖然說出來也無濟(jì)于事,旁人給予不了任何幫助,同情和勸慰僅停留在表面,但說出來或許就是轉(zhuǎn)移壓抑情緒的一種途徑。有時(shí)候,人需要傾訴,不能像發(fā)酵黃醬那樣,把心事和情緒憋在自己的肚子里爛掉。
她摘下漁夫帽,一把薅下頭上的黑發(fā),露出滿頭銀絲。這動作著實(shí)有些突然,嚇了我一跳——原來她戴著一個(gè)假發(fā)套。她笑著對我說:“四十塊錢買的,出來照相,戴上它臭臭美!”
說著,她打開遮陽傘,對我說了句“回家吃飯去嘍”,便風(fēng)擺柳枝、裊裊婷婷地走出藤蘿架。她的背影漸漸模糊,天藍(lán)色的傘面很是明艷,和秋日湛藍(lán)的天空融為一體……

 四川法制網(wǎng)
四川法制網(wǎng)
 法治文化研究會
法治文化研究會



 川公網(wǎng)安備 51010402001487號
川公網(wǎng)安備 5101040200148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