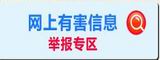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你怎么還不結婚呢?”旁邊的女生將椅子挪向我,挽著我的胳膊,“快看,這是我的小女兒,都兩歲了,可愛吧。”她拿出手機向我展示。
圖片里是一個扎著羊角的女孩,圓潤的臉上微微泛著紅,,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看著鏡頭。小孩長得和女生小時候很像,特別是那雙藏匿著星光的眼睛。透過星空,我的思緒飄回了過去……
那時候的鄉下,還能看見滿天的繁星。每當夜幕降臨,萬籟俱靜時分,浩如煙海的星星便一點點蔓上來,溫柔地擁抱夜空。
“你有沒有想過離開這里,去找爸爸媽媽?”稚嫩的童聲在我耳畔響起,我從草坪上坐起來,滿天繁星印入眼簾。良久,“我想,”我將頭埋進膝蓋,聲音微顫,“爸爸媽媽今年過年也不回來……我想他們。”
微風吹過蘆葦叢,發出蕭瑟吶喊。暮夜下,唯孩子的哭聲長鳴,斷斷續續,散入杯中化為舌尖的苦澀……
我放下茶杯,將那遠方的哭泣咽下,緩了緩神,面帶喜悅地看著那張小女孩的照片,稱贊道:“她很可愛,和你小時候一樣。”
她揚起微笑,一如當年般清澈。
如果沒有來參加這場小學同學聚會,我可能永遠再見不到她了,見不到那個夜空下問我想不想離開的小女孩。“你還記得你以前和我說過你的夢想嗎?你實現它了嗎?”茶盞之余我問她。她沉默半晌,扯出一個笑容,“哪還來的什么夢想,雖然每天都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但我覺得我現在的生活已經很好。”她轉過頭,“我很幸運,遇到一個我愛的、愿意陪伴我的人。我現在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我想用一輩子陪她們。也算……也算是彌補我童年的遺憾吧。”
“但你還年輕,你才25歲。”
“但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像我一樣,想親密無間,隔閡卻無處不在……我害怕。”
,后來,我作為支教老師回到了我出生的小鄉村。我曾以為我再也不會回來,回到這個充斥著孤獨與痛苦的地方。但是不知為何,當我看到它出現在選擇里時,我仍毅然決然地來了,或許是中國人對落葉歸根的執著,亦或是我內心的無法釋懷。
實施鄉村振興、精準扶貧的這幾年,確確實實給這個小地方帶來了巨大的改變。當我背著笨重的行李,站在嶄新的柏油路面茫然,也油然升起“鄉音無改鬢毛衰”的哀愁。遠處隱隱約約有人向我跑來。輪廓逐漸清晰,那是幾個黝黑的男童,剃著干凈利落的頭發,脖子上的紅禮巾在陽光下分外亮眼,散發著青春朝氣,加上的運動鞋因多次洗刷而微微泛白。
“你是我們新來的老師嗎?”第一個沖到我前面的男孩氣喘吁吁地問道。
“對,我是,你好啊!”我微笑地向他打招呼。
男孩的后面跟著一個微胖的中年人,正上氣不接下氣地喘著,良久,終于調整好呼吸。他向我伸出一只手,
“你好,我也是這里的支教老師,我姓葉,你叫我葉哥就行。”
據葉哥說,他已經在這里支教十年了,是唯一一個僅次于校長支教最長的人了。提起校長,他的眼神也變得柔和起來,
“我們校長真的是個很好的人,她今年已經64歲了。一開始這個學校就只有她一個老師。她培育出了無數優秀的學生,送走了一屆又一屆。”他面帶笑意,“我就是她的一個學生。”
平江中學是一所包含小、初、高的學校,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全校共有50多個老師,每個老師幾乎要同時教三個年級的學生,所以,教育局每年都會派很多年輕老師來支教,當然,也會有人選擇永遠留在這里,葉哥就是其中一人。
葉哥讓我先帶五六年級共兩個班,高年級相對聽話一點,不至于那么累。
輾轉反側,終于來到學校。模糊的記憶中,我依稀記得這里原本是一片荒地,貧瘠覆蓋了整片土地,連一抹綠也一并摧毀。而眼前的校園再不似往日荒蕪,但也沒有城市的繁華。它就安靜立在那里,灰白的墻體、殷紅的磚瓦,簡約且不落俗套,小巧又整潔干凈,響徹校園的讀書聲、歡樂聲帶給這片土地生機與活力。
來到這個學校已一月有余,漸漸地與班級里的孩子熟絡了起來。趁著周末,我打算去家訪一下班級里“最沉默”的一個孩子 。
泥濘小路變成了柏油路,人工水渠也砌上了水泥,稻田里忙碌的身影被收割機的哐哐聲替代。面對巨大的轉變,我順著腦海中依稀存在的原有模樣,找到了他家。
與世隔絕的竹林里,一縷炊煙在竹叢間繚繞,綠墻黛瓦也早已斑駁不堪,與山腳形態各異的獨棟洋房格格不入。
我敲了敲門,開門的的是一個年過七旬的白發老人。他看見我,露出微笑。眼邊的皺紋因笑意皺在一起,時光在他臉上留下了痕跡,卻似未染他半分心靈。
“老師你來了,京兒在做飯呢。”
“不用不用,我就是來了解一下情況,你們吃就行。”
屋內傳來一聲男聲:“老師,我已經做好了,你就來吃吧。”男孩抓著自己的衣角,略顯緊張地說道。
“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啦。”
整個吃飯過程非常愉快,我發現他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不善言談,相反,他是個很有思想的孩子。我問他的興趣愛好,問他的夢想。出乎意料的是,他幾乎看過學校圖書館里所有的書。我和他談紀伯倫,討論海明威,碗筷碰撞之間滿是歡聲笑語。
飯后,我和他爺爺坐在板凳上,看著他洗碗時忙碌的身影。我也曾想幫忙的,但卻被他“強制命令呆在原地”。
“京兒是個很懂事的孩子。”老人目光慈祥地看著他,“他爸爸媽媽在他兩歲的時候就去北京打工了,他從不哭鬧,也沒怎么要找過爸爸媽媽,從不讓我操心。”
我一直很討厭“懂事”這個詞,我從來不想當一個所謂的“懂事”的孩子,因為我懂事,所以我必須坦然地接受爸爸媽媽的離開;因為我懂事,所以我必須接受春節一個電話的祝福和一疊鈔票的親情。我被扼住咽喉難以發聲,我將我自己禁錮在“懂事”的牢籠,我掙不開,也出不去。
我是和李京一起走回學校的。當我問及他是否想他爸媽的時候,他突然抱住我大聲痛哭起來,多年的有苦難言與委屈終于在這一刻爆發出來。或許是因為有相同的經歷,我對他產生了深深的共情,我很能理解他現在的感受。我抱著他,輕輕地摸著他因為長期營養不良兒略顯病態的棕黃細發,背脊上突出的骨頭分外明顯,誰能相信這樣一具消瘦的身軀承受著多少連成人都難以忍受的心理壓力?
我慢慢蹲下身,雙眼微微泛紅,鼻頭發酸。我用手揩掉他兩頰的淚水:“可以和老師聊聊嗎?”我從未如此感激大學選專業時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心理學,畢業論文也是有關留守兒童心理方面的,使我有底氣將他拉出泥潭。
我沒想到時隔多年,我仍然能找到那片蘆葦地。正值皓月當空,繁星布滿蒼穹,月光下一大一小兩個影子并排坐著。我看著那個長長的影子漸漸縮小,最后盡然與那個小影子齊平。
“我想帶我爺爺離開這,去找我的爸爸媽媽。”
恍惚間,時空仿佛發生了錯位,眼前出現的是女生年幼的模樣。
“你有沒有想過離開這里,去找爸爸媽媽?”
我看見我拉住女生的手,緊緊擁抱著她,略顯激動地說:
“那就去找!你現在就給他們打電話,告訴他們你有多想他們,你想和他們一起生活,”我拉著女生跑了起來,途中被絆了幾跤,爬起來繼續跑,像一陣風一樣奔向村口電話亭。
“快,快給他們打電話。”我雙手撐這大腿,大口大口地喘著氣。
“好!”女生緊緊攥著電話,深吸一口氣后撥通了電話。
“喂,媽媽……”
“快看,這是我女兒,可愛吧。”旁邊的女生向我展示她女兒的照片,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我現在是個自由設計師,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我的夢想吧,終于實現了。我還擁有一個很愛我,尊重我的丈夫,我現在很幸福。”
杯子碰撞發出叮當悅耳的聲音,卻在下一秒摔碎在地。
“我想帶我爺爺離開這,去找我的爸爸媽媽。”男孩的聲音在耳畔響起。皎潔的月光勾勒著男孩瘦削的輪廓,他抱著雙腿,將頭埋進臂彎里。
“那就去找,”我從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機,遞向男孩,“選擇權在于你,你知道嗎,這通電話很可能改變你的整個人生。”片刻猶豫后他將手機拿在手里,輸入電話號碼。就在撥通之前,他抬頭注視著皓潔的明月,仿佛在做最后的道別,繼而看向我,眼眶閃爍淚水,“謝謝你,老師。”
“喂,爸爸媽媽,我想你們……”
不知不覺間,距離李京爸媽將他和爺爺帶去北京已經過去一年了,我也選擇永遠留在了這里,去幫助那些苦苦等待卻得不到回應的孩子們。我仍然會想起李京,想起那個從淤泥之中發現的星星。
十年后的今天,我一如既往在校門口等同學來上學,清點完人數后,一聲青澀又熟悉的聲音在我身后響起,他輕輕喚了一聲,
“老師。”(向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