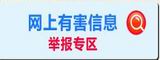2024年10月29日,是我終身難忘的日子。傍晚,我與老伴散步回家,穿過單位門前城市主干道的斑馬線時,我被一輛網約車撞飛20多米,眼前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見了!
飛來橫禍,命懸一線,生死未卜。眼前親朋好友、金錢美女、名譽地位......什么都消失了。不曉得什么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所住進的雖然不是太平間,卻是只聽說過、從沒見過的ICU病房。
突如其來的車禍引起親朋好友的高度關注,陪護的家人、探視的親友,時而給我帶來溫馨的關愛、美好的回憶。然而,親戚再親,也就是安慰;朋友再好,也就是看望;兒女再孝,也沒有太多時間和精力。要說最靠得住的,能夠天天陪護的就是老伴了。只是老伴年事已高,見到污物便反味,要晝夜貼聲護理完全癱瘓、不能自理的病人,可謂勉為其難。
幾天后我由ICU轉到普通病房,病房便冷落了,除了按部就班的醫務人員來來往往,身邊幾乎再沒有親人。之后3個多月,從早到晚,日夜陪伴身邊的只有一名護工,這位由陌生到熟悉的少婦,成為唯一朝夕相處、親密接觸的人。
我算是第一次接觸護工,由此對這位平凡的村姑,對這一不起眼的職業,開始有了嶄新的認識,且日益加深。
這段時間,身邊這位年輕的護工黃女士,替代了我的所有親人、包括母親和妻子等至親的位置,幾乎承擔了老伴所有的責任和義務,也發揮著子女有過之無不及的作用,自己才不至于是一個無依無靠、孤苦伶仃的可憐人,肉體上減少了不少痛苦,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慰藉。
那些日子,夢中出現的,睜眼見到的,伸手摸到的人,儼然就是朦朦朧朧的母親,勾出隱隱約約的童年記憶。自己這條生命,就是從母親的肉體上割下來的,吸著母親體內擠出的一絲絲乳汁成活,吃著母親喂養的一口口飯菜成長,聽著母親的搖籃曲、童話故事長大的。兒女的喜怒哀樂,無不牽動母親的心,傷痛更會十指連心。眼下我躺在護工懷里,仿佛就是躺在慈祥的母親懷里。想來母親已經早已作古,可眼前活脫脫當年后生的母親,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久違的母愛。
依偎在護工身上,似乎聞見了妻子身上特別的體香,眼前(特別是重癥期),這一幕幕竟然穿越時空浮現。我感受著護工親自烹飪的、一絲絲夾過來的粉絲,品味她熬制的一勺勺清香的稀粥,有些粗俗的肌膚接觸,別有情調,別有韻味。她那不均勻的氣息,像嬌嬌兒歌,像竊竊私語,像悄悄情話,最能催人入迷。每當他人(包括一些親人)掩鼻捂嘴逃之夭夭時,她那看起來粗糙的手,卻感到細膩無比,聞起來似乎有點異味,卻十分純正。她竭力翻動著我進行換洗抹擦,就像擁抱著愛人。若不是傷痛纏身,怎么也擋不住男子漢本能的沖動。我的傷痛慢慢在恢復,成雙成對,雙宿雙飛,成為我們重要的生活內容,洗臉洗澡洗衣,梳頭刮胡子,做伴侶,當拐杖,推輪椅,嗮太陽,相伴看夕陽......
病痛之中,最希望得到指導、幫助和鼓勵,我發現這正是黃女士的長項。她擅長心理慰藉,護理之余,講故事便成為重要方式,當成重要工作。故事內容不限,很廣,甚至突破了隱私。比如家庭故事、個人成長經歷,倒是無形中減輕了痛苦,增添了樂處,溫暖人心,成為這些日子最大的收獲。每天所有護理工作,似乎都像鬧鐘一樣設定好的。除去這些護理項目外,更多的“閑時”就是聊家常、講故事。
隨著傷情日趨好轉,她雖然嘴上仍然“大哥大哥”地叫得沁甜,我真把她當作“小妹”,甚至情人,有些難舍難分的感覺了。每天清晨醒來叫的第一個名字是黃女士;從早到晚見不到黃女士心里便空落落的,見到她后眼睛才會放射出光芒......深知,這只是一種莫名的、荒唐的夢魘。我知道,我們應該保持這種若即若離的關系,并非庸俗的關系,這才是純潔、長久的關系。可這樣的關系更加令人揪心,這段生活是短暫的,也是純潔的,留下的美好印象,或許會深深銘刻在我晚年生活的記憶中。
親身經歷,親身經歷,令人感慨與沉思。盡管人們的世俗觀念仍然根深蒂固,當今社會還有不少人對于工作并不穩定、完全伺候重癥傷病員的護工,還存在相當普遍的偏見:護工是當今社會最底層的群體,做的是天底下最骯臟、且傷風化的污濁事情。即使一些正在接受精心護理的傷病者,也對護工職業嗤之以鼻,甚至指責謾罵。但是,作為傷病者身邊最親密的人,護工給予減輕痛苦、慰藉精神的療效,無疑功不可沒。護工不僅不是低俗之體,所作所為并非下賤之事,她們就是重癥傷病員的保護神,就是高尚、純潔、講道德、脫離了低級趣味、有益于人民的福星。隨著老人社會的到來,護工與病人形成的醫患關系,將成為新時代和諧社會一種最活躍的人際關系。
作者:曹國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