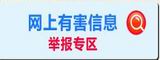在“文革”中的“清理階級(jí)隊(duì)伍,批斗牛鬼蛇神”運(yùn)動(dòng)中,我遭遇了一場(chǎng)劫難。
運(yùn)動(dòng)中,我成了“污蔑新社會(huì),惡毒攻擊社會(huì)主義制度”的壞蛋,成了“攻擊紅專道路,一貫白專”的典型,成了“臭味相投,妄圖建立反動(dòng)聯(lián)盟”的盟主……最為可怕的是成了“惡毒攻擊全國(guó)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yáng)毛主席”的萬(wàn)惡不赦的罪人!
這些罪名都鐵證如山:因?yàn)槲业娜沼浝镉浻叙I肚子的事情;因?yàn)槲业摹段乃嚲毩?xí)本》里有“我愛(ài)青磚,因?yàn)樗軗?dān)負(fù)起建設(shè)高樓大廈的重任;我不愛(ài)紅磚,因?yàn)樗郊t而沒(méi)有用途(當(dāng)時(shí)沒(méi)有機(jī)制磚,紅磚就是沒(méi)有燒好的磚,真的沒(méi)有用途)”的句子;因?yàn)樵诮o同學(xué)的留言中,有對(duì)出身不好的同學(xué)的贊美……因?yàn)樵谝皇最}為《斥牡丹》詩(shī)里,有“花王,牡丹/牡丹,花王/我問(wèn)你/這么久了/你的責(zé)任盡到了萬(wàn)分之幾”的句子… …
日記和《文藝練習(xí)本》是我主動(dòng)交上去的,我認(rèn)為那里面沒(méi)有見不得人的東西,誰(shuí)知道竟會(huì)是這樣的結(jié)果呢?
年輕的我嚇壞了,我怎么擔(dān)得起這樣的罪名啊?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我不是這樣的人啊!我委屈,我苦悶,我惶恐!我多么希望能和人談?wù)劊嗝聪M苡袀€(gè)機(jī)會(huì)傾吐,多么希望有人給我一點(diǎn)安慰……可是,罪名深重的我能和誰(shuí)談,誰(shuí)又能和我談,敢和誰(shuí)談,誰(shuí)又敢和我談呢?誰(shuí)能給我機(jī)會(huì),誰(shuí)敢給我機(jī)會(huì),誰(shuí)能給我安慰,誰(shuí)敢給我安慰呢?
然而,當(dāng)時(shí)的我,是非找人談?wù)劊钦覀€(gè)機(jī)會(huì)傾吐不可了。不然我要垮掉了。
我終于想到了辦法!
我以“匯報(bào)思想”為名,找了一位當(dāng)時(shí)擔(dān)任領(lǐng)導(dǎo)職務(wù)的老同學(xué)。挨餓時(shí),他喊餓比我喊得還兇。
在“匯報(bào)完思想”后,我說(shuō):“最后,我有一個(gè)請(qǐng)求,請(qǐng)您以老同學(xué)的身份,回答我:我真如批判的那么壞嗎?”
他沒(méi)料到我會(huì)這樣問(wèn),一怔,然很快鎮(zhèn)定下來(lái),說(shuō):“怎么不是?”
我氣極了,說(shuō):“那時(shí),你也喊過(guò)餓,你不也是‘污蔑新社會(huì),惡毒攻擊社會(huì)主義制度’嗎?”
他說(shuō):“當(dāng)然不是,我們貧下中農(nóng)對(duì)舊社會(huì)懷有深仇大恨,對(duì)社會(huì)主義無(wú)比熱愛(ài),怎么能和地主崽子相提并論呢?”說(shuō)完,急匆匆地走了。
我明白了,這一切都是出身惹的禍!可明白有什么用呢?這出身是沒(méi)法改正的啊!而今的我,是黃泥巴落到褲襠頭——不是屎也是屎了!誰(shuí)叫我沒(méi)個(gè)好出身呢?我好眼紅那些出身好的人!甚至眼紅那些出身雖然不好,卻什么也沒(méi)有寫或者干脆不會(huì)寫的人!我為什么要識(shí)字?為什么要寫那些勞什子?
我徹底地心灰意冷了,聽命運(yùn)安排吧!成天低著頭來(lái),埋著頭去,不和任何人說(shuō)話,甚至不和任何人對(duì)視。痛苦之時(shí),便一個(gè)人守著墻角發(fā)愣。
一天,我又守著墻角發(fā)愣,背后傳來(lái)了腳步聲。我沒(méi)有回頭,沒(méi)有必要回頭,因?yàn)榇藭r(shí),人人對(duì)我避之不及,來(lái)者,不會(huì)和我有關(guān),不過(guò)是從這兒路過(guò)而已。
可是,腳步聲卻在我身后停住了。我驚異地回過(guò)頭,是高中時(shí)的同學(xué)余國(guó)英!她關(guān)切地盯了我一眼,手一抖,一個(gè)小紙團(tuán)落在了我的面前。隨后,她轉(zhuǎn)過(guò)身,無(wú)事般地走了。
我急急地?fù)炱鸺垐F(tuán),展開,上面寫著:“現(xiàn)在,不是評(píng)功擺好的時(shí)候。”一股暖流頓時(shí)從我心里升起:我并不如批判的那么壞,有人知道我的好!他們現(xiàn)在沒(méi)說(shuō)我的好,那是因?yàn)椴皇菚r(shí)候!我感到了無(wú)比的安慰,望著她漸漸遠(yuǎn)去的背影,我心里充滿了感激!
為了不給她添麻煩,我把紙團(tuán)毀掉了。
五十年多過(guò)去了,我仍忘不了那雪中送炭的小紙團(tuán),它是化解我心靈痛苦的良藥,是剔除我心理腫瘤的手術(shù)刀!它安慰了我的委屈、苦悶、惶恐的心靈,幫助我捱過(guò)了那段心驚膽顫的歲月……(徐敬德)

 四川法制網(wǎng)
四川法制網(wǎng)
 法治文化研究會(huì)
法治文化研究會(huì)



 川公網(wǎng)安備 51010402001487號(hào)
川公網(wǎng)安備 51010402001487號(h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