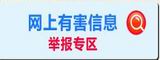點檢春風歡計,惟有詩情宛轉,余事盡疏殘。彩筆題桐葉,佳句問平安。
——《水調歌頭·解衣同一笑》
啟點
在眉山,有這樣一個小鎮,喚為多悅。我來到這里,已經大半年有余。在此之前,盡管工作了些許年頭,但我一直都固執地認為,自己從來不是一個合格的基層工作者,只因我始終貪念于對過往的記憶,并且習慣感知于熟悉的環境,所以換做從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最終會選擇背井離鄉,來到在這樣一個平凡的小鎮里生活、工作。
或許,是冥冥之中的因緣,帶我來到了這里吧。
我還記得,那是一個初春的時節,馱著一包包的行李,獨自悠悠地開著車。在穿過狹長而寒冷的隧道,駛過一眼望不到頭的高速公路,不多久,大片的綠色植被,巍峨的大山,把彼時的道路拉得老長老長,被一點點拋在了身后,明晃晃的太陽打在車窗上,讓人的眼睛,也不自覺地瞇成了一條縫,耳畔,不時傳來音響里干澀的樂聲——
“紅塵啊滾滾 癡癡啊情深 聚散終有時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至少夢里有你追隨……”
隨著面前從未見過的景色不停變化,仿佛間,自己像是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時空旅行。一直到抵達目的地,撥通手中最為熟悉的電話號碼,向遠方的愛人及父母報了平安之后,他們的囑托才將我從恍惚變得清醒——平安就好,注意安全。
大半年過去后,現在回想起彼時彼刻,我才敢確定,那的確就是一段關于時間的旅行。自參加工作以來,因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總會收獲不一樣的經歷。還記得大學才畢業時,在陌生人一聲聲的“騙子”的嘈雜聲中分發廣告傳單,賺取了所謂的人生的第一桶金;后來去了草原,以新聞記者的身份與牧民們打了大半年的交道;在人生第一份工作面前也曾“勇敢”辭職,一心要去大城市體驗都市的生活,每天重復著方程式的節奏;在此之后,妥協于繁忙而拮據的生活,選擇了公考,在2018年,我如愿成為了一名干部,也成為了一名駐村工作隊隊員……
落葉飄落在大地上,沒有方向,更沒有坐標,人亦是如此,我們都被命運所推動,最終都會擁有屬于自己的遠方。我深知自己,對青春的不舍,但我亦深知,哪怕萬般留念,想要不負未來,唯有朝過去揮手告別,而那些晦澀而陰郁的情感,也注定會如同被拋在身后的風景一般,消散不見。
長河
多悅鎮,理所應當地成為了我的棲息之所。這座小鎮擁有四川盆地鄉村的典型的濃郁生活氣息,長著青草的路檐,緊湊而樸實的民房,夜里會有忙碌了一天的男人們三三兩兩聚在燒烤攤上擺著龍門陣,而平日寂靜的場鎮每隔幾天便會因為十里八村的人們“趕場”而熱鬧……日子一久,農村的生活在恍惚間便容易讓人產生錯覺——距離鋼筋鐵骨的都市生活,其實渺小的我們,或許還很遠很遠。
只不過,這些于我而言,其實也并無多大差別。如果,硬要說在大半年里,這里于我而言,有什么特別之處的話,我想,大概便是往日在藏區所感受的那股蒼茫,慢慢被平凡而磅礴的水汽所替代,靈魂也變得溫潤了起來。
但是這份溫潤起初卻并沒能我的內心帶來任何一絲寧靜和安詳。每當想起遠在他鄉的家人,和過去的光景,內心的千頭萬緒,便涌上心頭,猶如困獸。那是一種復雜而統一的對立情感,不停拉扯,相互糾纏,最終拉扯出兩個自我,一個在田間野地里獨自寂靜,一個在燈火輝煌處黯然惆悵。
子來多悅豫,王事寧怠遑。三旬無愆期,百雉郁相望。
而在這個虛妄情感尚未平息的沉悶熱夏,我也去見了多年未見的一些老友。我們因不同的理由來到了同樣的土地,而在很多個夜晚,我們也會因枯燥而聚在一起,因饑餓而一同進食,就像一群居住在深山叢林中的動物一樣,滿足于對彼此的聲聲寬慰,滿足于對食物的細碎咀嚼。“下一次,有機會的話,再一起聊點什么吧……”抱著這樣類似而細小的念頭昏昏欲睡,日子,仿佛也開始變得簡單而又充滿期待。
但不得不承認的是,物質始終大于精神,生活也始終大于妄想,感同身受的認知情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變得越來越少,久而久之,忙忙碌碌的大部分的我們,活成了冷暖自知的狀態,再也沒有多余的情感或事物,能耗費我們無數不多的時光。或許,也正因如此,我始終堅定地認為,相比一個人對于生活的自怨自艾,我們更需要的,其實是對他人情感的無限貪婪。
人事聚散,歲月迢迢。時間,不可追,不可尋,明天無法揣測,當下瞬息萬變,但它卻是最好的見證,與人安慰,與人期待,平平安安,其實便已足以。
因為人世間何處歸途,何處天涯,誰又說得清楚呢。或許遠方亦是歸途;或許故鄉亦是天涯。心若荒涼,日日皆是凄苦飄零;心若安恬,其實處處皆是牧歌田園。
流沙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1927年初,22歲的奧斯特洛夫斯基已經完全癱瘓,即便病痛折磨,他卻依然堅持以創作代替心中的革命,可惜,最初的手稿,早在郵寄的來回途中遺憾丟失。而直到1933年,《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才真正得以完成。這本書,曾經陪伴了我無數個寂寥的夜晚。
孩提時候,其實是看不懂這書的。隨后,當我自認能讀懂這本書的時候,我早已與如今的妻子相戀,我大概是,從那時候起,也遇見了自己生命中的“達雅”。
那個時候,她還不是一個妻子,也還不是一個母親。我們相隔千里,唯有一次次地通話,一次次地視頻,去支撐著對彼此單薄的愛情。我們會聊彼此看過的電影,彼此看過的書,彼此看過的風景……
——“那么,麗達也好,達雅也罷,究竟誰對保爾才是最重要的呢?”
——“我想,或許都不重要吧?”
——“為什么呢?”
——為什么呢。我說不上來。我無法去深究縈繞在腦海里那些奇特的問題。正如眨眼間,我心中的孩童尚未長大,而我現實中的孩子卻已蹣跚學步,即將步入學堂。家人的日常開支更需要我去維系,父母日漸老邁的身體更需要我去牽掛,而上級交付的工作任務遠遠比自己的只言片語更為重要。
“不要出任何意外”。成為了每一個平凡的我們,畢生的最終追求。
彼岸
上個月,記得還是休假的時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在即將返崗的那個夜里,嗅著妻子和女兒的鼻息,我做了一個很長的夢,夢里盡是望不見頭的人海,我牽著妻子的手,抱著孩子在人群里徘徊穿梭,最終在一個旋轉木馬面前停下了腳步。那是在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巨大的旋轉木馬,我倚靠在欄桿外,望著妻子將女兒摟在懷里,坐在木馬上放聲大笑著,耳畔縈繞著的音樂,和她們的笑聲融在一起。自己竟也不自覺地笑出聲,醒了過來。
而第二天的天空,放晴得很早,陽光溫暖的程度恰到好處,像是孩童的手一般,輕輕撫摸著我的鼻尖。匆匆喝過幾口妻子熬的白粥后,我便踏上了返崗的路。臨走時,她反復叮囑我,記得要按時吃早餐,天冷了,一定要添加衣物,還有就是不要總抱怨工作,要好好上班。
那一瞬間,我是多么想和她分享昨夜那美妙的夢呀。但始終又怕孩子醒來,只得匆忙啟程趕路。
那一天駛過盤旋的高速公路,看上去像是一條蜿蜒的河。哦,對了,就像曾經從事河長制工作時,經常巡護的那條河,即使肉眼看不見,每年河道的走向總會有些許變化,河床的高低也會隨著汛期的更替而有所升降,而無數的砂石盤踞河谷,堆積在一起,像是一座座沉默的雕像,守護著蕩漾的河流,守護著兩岸的植被,守護著沿河的萬家燈火,也守護著一方百姓的平安。
而相比于對虛妄事物的情感追求,我想,這種凝聚在一起的沉默力量,其實才是推動時間和故事不停向前發展的唯一理由。平安度過此生必經的修行,也為他人悲苦喜樂的蜿蜒大河,筑起足夠支撐的堅實谷底——
我想,石頭們,正是做到了這一點吧。
(趙國棟)

 四川法制網
四川法制網
 法治文化研究會
法治文化研究會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