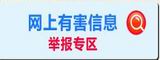像夏日雷雨,小弟的神精又突然崩潰了。他向鄰居、熟人不斷絮叨:“有人要害我,有的人要害我啊……”
我非常生氣,卻無可奈何。
我們一共有五兄妹。早年,父親臨終時曾告誡我:“注意你老幺兄弟,他會走極端的!”我不以為然,覺得小弟與大家一樣,好端端的,怎么會走極端呢?
小弟生于1962年。1982年進彭山陶瓷廠上班。1985年,與附近一農家姑娘自由戀愛結婚。1987年有了女兒。不久,單位生產不景氣,工資少,也不能按時發放。小倆口有了矛盾,弟媳開始要求離婚……就從這時起,父親的預言出現端倪:小弟不愿意妻子離開,向她保證,自己一定會養活一家人。為了證明自己的決心,他竟然操起萊刀,突然把自己的一截小指砍了下來。
他終究沒能留住妻子。弟媳離婚回娘家了,女兒留給了小弟。小弟天生少言寡語,如今更加沉默不言。不久單位解體,小弟分到400多元譴散費。他沒有人脈,也沒有什么技術,揣著這點譴散費成天發愁——往后,拿什么養活女兒與自己呢?于是,他每天買3分錢一把的空心菜、菠菜,企圖延長那點現金的使用時間,父女二人日漸消瘦……
數月后的一天,他偶遇一個同學,同學聽了他的訴苦后,說:“我們五金廠不也垮了嗎?你可以像我一樣,拉三輪掙錢嘛!”小弟說自己總共100多塊錢,最多能買下三輪車的輪子。
“你傻呀!不知道去租嗎?有的有錢人腦袋活絡,買了多輛上了牌照的三輪,專門出租給別人,每天才2元錢的租金哩!”小弟眼前出現彩虹。他知道,當才華配不上夢想的時候,便要腳踏實地的出力流汗。他虛心向同學學習:怎樣敏銳地用雙眼,捕捉某個路人需要叫三輪;怎樣勤快地把乘客的貨物不要報酬幫他扛進家,以圖回頭客;怎樣在深夜或雷雨交加之時冒著嚴寒、風雨勤快蹬車多掙錢。他與同學常常在夜里擦肩而過,他們會互相詢問:
“如何?”意思是生意好不好。
另一個會回答“好!”或者“撇!”
子夜時分,生意好的一個會在交錯時對另一個說:“這趟跑了,到我家來喝酒!”
他們互相鼓勵。他們認為,生活,一定會有曙光。
后來他們發現一個商機:在縣醫院門前等候,乘客多,而且有意外收獲,救護車拉回出了車禍的傷者,有時需要多人去抬擔架。抬了擔架,傷者家屬就會給較多錢。
黑惡勢力在許多地方都存在。一個三輪車團伙夜晚襲擊了小弟,把他痛打了一頓后,警告他:再在縣醫院門前看到他,不會再客氣,不但打他,還要把他的三輪車給砸了!
小弟從小膽小怕事、逆來順受。他把租來的三輪退了,一個人躲在家里療傷。
就在這時,社區陽光般出現了。社區主任何老漢來到小弟家,送上慰問品后,流著淚說:
“老幺啊,伯伯對不起你啊。平時再忙,怎么沒忙到點子上呢,你看,你過得這么難,我們咋就沒有深入了解呢?放心!你馬上寫申請,我即刻去申報你的低保!”
第二月,小弟便領上了每月50元的低保金。社區干部決心要給小弟更多幫助,他們不遺余力,多次聯系,最后在縣職高給小弟找了個穩定的后勤工作。
小弟安安穩穩的在職高上了4年班——看大門,收拾男生宿舍。4年過后的某一天,小弟找到我,要我給他拿主意:郭校長調離職高了,接任的領導已經在換編外人員了,他們要換上自家的親戚朋友……“我想用兩個月的工資買點煙酒送給郭校長,你說,買啥子品牌的煙酒呢?”
我很生氣:郭校長都調走了,鞭長莫及,況且他也不好回來插手啊!小弟堅持認為,郭校長畢竟當了那么多年的領導,繼任者得買賬啊。
在我強烈反對下,小弟最終還是妥協了。因為沒有送禮,他生怕失去工作,成天惴惴不安,行為開始反常。輪休在家時,他時不時會叫兩個嫂嫂反復出門,到街上去觀察。他吩咐她們:“看看鐵匠鋪門外的那輛面包車在不在!”
次數多了,兩個嫂嫂很生氣:“面包車一會兒在,一會兒又不在。在與不在與你相關嗎?”她們逼問小弟,到底是啥事?!
小弟十分不安,他懷疑面包車里的人要害他。
小弟最終被職高裁員了。在職高工作幾年,他攢下了4000多塊錢。他身累心累,終于糊涂了,成天疑神疑鬼,總感覺有人要加害自己,甚至加害我們一大家族人。可有一點,他卻一點也不糊涂,知道過日子需細水長流。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父女二人得填飽肚子呀!他又開始了每天一把便宜青菜的生活……
2015年,好消息接踵而至,北外街棚戶區改造,小弟沒花一分錢,分到兩套房,每套60平米。陶瓷廠原廠房被城投公司收購,小弟分到8000多塊錢。然而小弟仍然快樂不起來。問他許久,他才說,自己快60歲了,社保都沒買,晚年怎么過?雖然有兩套房子,但是什么家俱都沒有,怎么住呢?
社區干部、原陶瓷廠領導、甚至連協調城投公司與陶瓷廠之間的律師都行動起來。他們調出小弟的檔案,與社保局接洽,小弟是高溫工,按政策應提前退休。得到社保局認可后,我也忙起來,把他的一套60平米的住房賣了25萬塊錢,補交了社保金,剩下的錢把僅存的一套住房簡裝了,又買了家俱家電。小弟在2017年領到了每月2000多元的社保金,也搬進了久居福小區新家。
謝天謝地,小弟終于不糊涂了。他一清醒,善良的天性即刻回歸,他認為幾個哥哥都有孫子了,很繁忙,給老母養老送終的事,由他自作主張,堅決把母親接到他那60平方的小房里。雖然我們會給母親生活費,但一日三餐,洗洗涮涮都是小弟一人操勞啊!小弟把母親照顧得非常好,直到她94歲高齡,才安然地無疾而終。
小弟一直都很節儉。女兒早已出嫁,領社保金數年來,在我的叮囑下,他每月用錢都不到1000元,剩下的錢存起來,以后有病痛時,不用女兒掏腰包。目前,他已存了10萬元!
可是,半個月前,好端端的小弟又犯病了!
拆遷戶的房產證由物業統一辦理,物業要求小弟:凡是已離婚的,需拿上與前妻的離婚證來認證,方能領房產證。小弟囁嚅說,離婚證早都弄丟了,咋辦?物業告訴他,去法院查存檔,復卬后交來就行。
前妻一直是小弟內心的傷痛。查到存檔,看到前妻當年對自己的指責、控訴,小弟馬上就糊涂了。他或是跑到大街上喃喃自語,說有人要加害他;或獨自坐在小區花臺上望著天空發呆。

我們趕快去找社區。社區領導高度重視,立刻撥打區精神衛生保健院的電話。區精神衛生保健院回復:請馬上送到保健院來,如果病人亢奮、不愿意配合,打電話來,我們派 護士和車來接走!
我要真誠地感謝黨,感謝政府,感謝社區與保健院領導!你看,雖然我的小弟是個社會底層人士,但是,黨與政府的各級領導卻沒有把我小弟當成無足輕重的人,真正把他當成一個共和國的公民,給予了充分的尊重與人性化關懷!
3月14日,我去區精神衛生保健院探望小弟。他的狀態明顯好轉,希望可以出院。我十分同情小弟,馬上便去找他的主治醫生。主治醫生告訴我,小弟的病情雖然樂觀,但還得觀察,鞏固治療效果。他要求我過一個月再來看看。
我 還知道,保健院每月只收取每個病人500元費用,包括藥費、一日三餐、理療康復等等所有費用!
我相信,我小弟的被迫害妄想癥一定會很快康復。
真好啊,有黨和政府給小弟作支撐,真好……

 四川法制網
四川法制網
 法治文化研究會
法治文化研究會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
川公網安備 51010402001487號